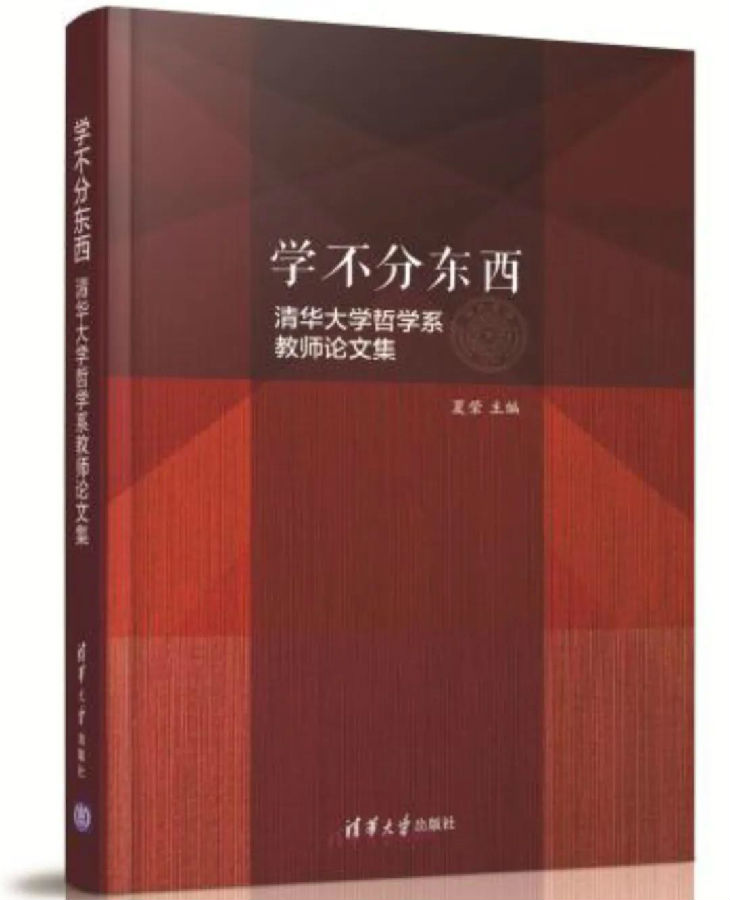
欣逢清华大学建校110周年庆典,清华哲学系的同仁欣然集文以纪之。大约是因为我曾受命负责清华哲学系的复建工作凡十年有余,料理文集编辑事宜的夏莹教授便令我为之一序。我以为,此序当由现任系主任宋继杰教授为之更好,但继杰君习惯于藏锋留白,不露声色。编者于是便盯上了“始作俑者”的我,虽多惶恐,几经推辞不果,最终只好勉力为之,以承我之“始作俑者”的责任。因为这部文集是清华哲学系同仁们的合力之作,我之为序也不敢简单从事,更不能以形式主义的方式敷衍塞责。几经考量,我决定借此机会,简要地回味一下清华哲学系和清华哲学的成长历程,庶几近乎一种学术家谱式的自叙,鉴于斯事斯时之不凡,这或许是一种较为平实、也更近乎“合情合理”的序言方式罢!
如所周知,北京大学哲学系和清华大学哲学系乃现代中国大学两个最早的哲学系。很幸运,我有机会先后在这两个哲学系执教,而且与两者都有着某种学术亲缘关系:北大哲学系是我的研究生母系,我曾在那里学习、工作近16个春夏秋冬;清华哲学系则是我已经工作21年且将要奉献余生的学术共同体,况且,她还是业师周公辅成先生的研究生母系,师爷吴宓先生更是清华国学院的创始院长,而我门下的博士开门弟子唐文明教授,自北大哲学系博士毕业后也一直执教于清华哲学系。师徒“四世同堂”,也算得上是一种学术奇缘吧!
我曾在应约撰写的《“中国现代性”中的哲学知识刻画》一文中,集中比较过北大清华两个哲学系在哲学教育取向和哲学知识生产方式等方面的异同,进而简要分析了她们对中国现代性知识体系的哲学影响。[1]而在另一篇题为《学统,知识谱系和思想创造》的文章中,我大致地回顾了清华哲学系的“系史”,并对清华哲学系的学术谱系做过一种批评反思性的初步分析。[2]在我个人的学术理解中,大学的学科系既是一个专业知识教育和专业人才培养的“基地”,更是一个专业知识创生、传承和创新的学术共同体,因之也必定生成其独具特色或风格的知识谱系和学术传统(我将之简称为“学统”),进而,如何生成、保持、传承和弘扬其知识谱系与学术传统,便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
清华哲学系称得上是一个既古老又年轻的哲学系。谓其古老,是因为她自1925年创立起已近百年,曾与更早一些建立的北大哲学系并称为中国高教史上两个最早的哲学系,两者曾经共同创造过“双峰并立,各显千秋”的中国近代哲学的先期辉煌。当然,这只是相对于中国的现代大学建制史来说的,若比起牛津、剑桥这些近千年的名校哲学系来说,她们都还算不上“古老”,毋宁说还太年轻。谓其年轻,还因为清华哲学系如同所有的清华文科院系一样,早在1952年那场著名的“院系调整”中,被并入北大和稍后建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直到2000年世纪之交,她才在清华文科的整体复建中浴火重生。这样算起来,清华哲学系的生命历程迄今还不足半个世纪,正在“不惑”与“知天命”之间,而自复建至今方20年开外,正值青春年少时。我曾诗意地期待,清华哲学系的复建有如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期待她能够光复并续写其堪称辉煌的学统或“家谱”。
清华哲学系是清华由“赴美预备(培训)学校”转升为大学之后五个最早的文科学系之一(余者为中国文学系、西洋文学系、历史学系、社会学系)。清华大学的前身是1909年7月(宣统元年)创建的“游美肄业馆”,在同年派出美国的留学生中即有一名赴美学习哲学的学员。次年,也就是1910年,年方18的胡适考取“清华留美预备学校”,不久即赴美学习哲学。他先入康乃尔大学农学院学农,但很快便转至文学院学习哲学,1915年再转校哥伦比亚哲学系,师从当时最著名的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大师杜威(JohnDewey)先生学习哲学,1917年,他以以《先秦名学史》为题,完成其博士论文并通过答辩,成为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第一位哲学博士。1917年秋,胡适先生回国,接受当时北京大学新成立的“哲学门”执教,讲授中国哲学。可以说,胡适先生是从清华学堂走出来的第一位清华哲学学子。
1911年4月(清宣统三年)“游美肄业馆”改为“清华学堂”(实际为“学院”,即“Tsing HuaCollege”),在其教学课程体系中即开有“哲学教育”课程。“清华学堂”即是清华大学的前身,1911年也因此被视之为清华大学的创始年,距今将近110周年。1912年,“清华学堂”改名为“清华帝国学院(堂)”,并配置英文专名“Tsing Hua Imperial College”,但很快又改回“清华学院(堂)”(“TsingHua College”,方便理解起见,我把“学堂”改译为“学院”),剔除了原英文中的“帝国”(“Imperial”)字样。1925年,清华国学院成立,吴宓先生任创始院长,有幸延聘到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四大导师”。1926年,“清华学院”正式改为“国立清华大学”后,终于结束了近四年校局不稳、校长频换的“动荡”时期。国民政府派毕业于北大的罗家伦先生接管清华,自此,清华大学迅速崛起,进入快速发展的初盛时期。顺便说一句,从清华走出去的胡适之先生后来成了北京大学的校长,而学成于北大的罗家伦先生则成为国立清华大学的校长,至1931年,由梅贻琦先生接任清华大学校长。胡适和罗家伦二位掌门人都在各自效命的大学建校之初做出了堪入史册的大成就,北大清华常互称“隔壁”,友邻互助互竞并在互竞中携手共进,至今弦歌不绝,实在是值得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大书一笔的重大叙事(故事)。
国立清华大学建立之初,即建立文、理、法三大学院,内含12个学科系,哲学系赫然在列。起初,学校指派教授语言学的赵元任先生负责哲学系的课程建设,并设计开设当时中国阙余的逻辑学课程,因起始课程讲授任务过重,又面临全新课程的开设,赵元任先生感觉难以独自应付,遂推荐正在欧美游学的金岳霖先生担任清华哲学系主任,并负责开设逻辑学课程。事实上,金先生的博士专业原本是政治哲学,但他在欧美游学期间接触到罗素等分析哲学家,原本对政治缺乏兴趣的他倏然对逻辑学发生了极大兴趣,借游学欧美的机会自学逻辑学和分析哲学。这似乎再一次印证了那句教育名言:“兴趣是学习的第一导师”。回国受聘于清华哲学系之后,金先生出任清华哲学系的创始主任,开始设计和创建逻辑学课程体系,并自编教材。可以说,正是金岳霖先生最早引进欧美逻辑学学科,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史上逻辑学这门经典哲学学科的奠基者。金岳霖先生身负清华哲学系的创始者和逻辑学中国开设的奠基者两重角色,确立了他在现代中国哲学史上的独特地位。
不过,准确地说,1926年正式成立的清华哲学系最初只有教师一人(31岁的教授金岳霖),学生两人(沈有鼎、陶燠民),颇有点人们所熟知的“一条板凳,一头坐着一位长者,另一头坐着一位年轻人,当两人开始对话,大学便产生了”的美丽的大学传说,故此,有人把这种单枪匹马式的起始状态戏称之为清华哲学的“自我风流”时刻,倒不失为一种有意味的调侃。此后26年,清华哲学系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并很快呈现人才济济、硕果累累、风格卓越、学术繁荣的“清华学派”(王瑶先生语)景象。作为清华哲学系的创始者,金岳霖先生先后完成并出版《逻辑》(商务印书馆1936年出版)、《论道》(商务印书馆1940年出版)和《知识论》(成书于西南联大抗战时期,因战火遗失,最后重写,由商务印书馆1983年始得出版)三部代表作。其后受聘为清华哲学系教授的冯友兰先生,入职不久便完成并出版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上卷1931年、下卷1934年出版),该书成为我国第一部完整的《中国哲学史》;紧接着,他又在抗战最艰难的西南联大执教时期完成并出版其哲学代表作“贞元六书”,即:《新理学》(1939年)、《新事论》(1940年)、《新世训》(1940年)、《新原人》(1943年)、《新原道》(1945年)和《新知言》(1946),并于1929年接任金岳霖先生担任清华哲学系的第二任主任。金、冯两位先生作为清华哲学系的早期创建者,不仅为清华哲学系的创立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确立了学术与教育的高标,而且也是“清华哲学学派”的创建者和学术领袖。1930年代受聘于清华哲学系的张申府、张岱年两兄弟也对清华哲学学派作出了重要贡献,前者率先在清华大学开设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据说他是在中国大学第一个正式开设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的人;后者于1936年完成出版其首部哲学代表作《中国哲学大纲》,并在1948年出版其另一部哲学代表作《天人五论》。同时期先后进入清华哲学系的教师还有梁启超先生(兼职)、赵元任先生(兼职)、汪鸾翔先生(清华大学校歌的词作者)、陆懋德先生、邓以蛰先生、贺麟先生、林宰平先生、贺自昭先生、潘怀素先生、沈有鼎先生和稍后引进清华的王玖兴先生等诸多哲学名家,可以说,至上世纪30年代后,清华大学的哲学系已然十分壮大。张申府先生在他的一篇回忆文章中,甚至自豪地说出了“本系在全国大学的哲学系中又未尝不可成为最强之一系”[3]的话,事实上,一直到1952年清华哲学系被迫“调整”前夕,清华哲学系的确已经呈现出群贤毕至、枝繁叶茂果硕的繁荣景象,不仅堪称当时中国大学中的哲学翘楚,而且堪比国际名系。殊为可惜的是,“仿苏式”的“院系调整”,竟使风头正劲的清华哲学顷刻间轰然倒下,令人至今唏嘘不已![4]
清华哲学系“被调整”后,金岳霖、冯友兰、张岱年、邓以蛰、贺麟等先生进入北大哲学系,金先生担任北大哲学系主任,王玖兴、周礼全等先生稍后追随被国家钦点负责创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金岳霖先生,成为社科院哲学所的早期创建者。我想坚持强调指出,老清华大学的哲学系就是这样被“解构”、被“消失”的,无论对于一所大学,还是对于现代中国高等教育事业来说,这都是一件非同寻常的“教育事件”。老实说,自我进入周公辅成先生门下起,这件事常常成为我们师徒门内叙事的话题之一,也大概也是我本人在大约半个世纪后,有些孟浪而又带有几分悲壮地选择悄悄停止沐浴未名阳光转而欣赏荷塘月色的一个主要却又是“密而未宣”的缘由吧!
自上世纪80年代起,清华开始复建其曾经强大的理学群(先是数、理、化、生,继而医学)。至上世纪90年代,清华着手复建其曾经同样强大的文科群,先是创建“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特聘张岱年先生为创始所长,后建设中文系、历史系、扩充外语系等基础人文学科系,再建人文社会科学学院。1999年四月,我接受邀请,在尚未办理好人事手续的情况下,只身来到清华,开始复建清华哲学系的工作。同年六月,邹广文教授从山东大学调入清华,不久,王晓朝教授从浙江大学调入清华,我们三人组成了复建清华哲学系的“草创班子”。随后,我们开始引进教学“骨干”和青年教师,先有胡伟希、卢风、肖鹰、肖巍等教授从校内外陆续加入,后从北大、社科院哲学所引进唐文明、彭国翔、宋继杰三位青年才俊,加上原有的吴倬、赵甲明、唐淑云、田薇、唐少杰等老师,到2000年春,复建中的新清华哲学系初具雏形,至五月初正式宣布建立。随后,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加强了人才引进的力度和广度,先后引进过李存山、王路、蔡曙山、贝淡宁(Daniel A. Bell)、王中江、陈来、刘东、韩立新、刘奋荣、樊浩(樊和平)、曹峰、黄裕生、唐浩等教授,虽然他们中有些人因为各种原因又先后离开了清华哲学系,但迄今为止,复建后的新清华哲学系已然拥有了30多位教师,呈现出各个二级学科学术带头人强力齐备、整体团队的年龄结构日趋合理、各分支学科配置完整、充满生机活力的大好局面,并在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逻辑学、伦理学等方面获得优势发展。目前,清华哲学拥有清华大学首批文科资深教授二人(陈来、万俊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三人(万俊人、刘奋荣、丁四新)、青年长江学者一人(夏莹),另有国家一级学会会长两人(陈来、万俊人)、二级学会会长一人(黄裕生),国务院学科评议专家委员会委员一人(陈来),国务院学科评议专家委员会哲学组成员一人(陈来),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一人(陈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专家评审委员会专家评委二人(万俊人、陈来),中央“马工程”首席专家兼召集人一人(万俊人),拥有国际校级合作科研平台一个(清华大学-阿姆斯特丹大学逻辑研究中心、校级科研平台三个(国学院、道德与宗教研究院、马克思文献研究中心)、院级科研平台若干。在教学、科研、国际合作等多个方面均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
另外,我们还在学校特别给予的优惠资源与优先扶持政策的支持下,还特设了“金岳霖逻辑学讲席教授(团)”、“贺麟西方哲学讲席教授(团)”和“冯友兰中国哲学与伦理学讲席教授(团)”三个特聘讲席(团)。目前,“金岳霖逻辑学讲席(团)”(由Johan von Benthem, Martin Stokhof, Dag Westerstahl, Jeremy Seligman四位国际著名的逻辑学和分析哲学教授组成,他们中,一人是为荷兰皇家科学院和美国人文科学院的双聘院士,一人为荷兰皇家科学院院士,均为所在大学的讲席教授)已开聘三年,成效卓著。“贺麟西方哲学讲席(团)”(由Ortfried Hoffe, Michael Beaney, Charles Travis, Robert Stern四位欧美著名哲学家组成,他们中,有德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分析哲学史学会的主席,有英美权威哲学杂志的主编,均为所在大学的讲席教授)已正式受聘到位。“冯友兰中国哲学与伦理学讲席”即将开放。这些特聘讲席教授都来自欧美著名大学前沿,他们先后开出十多门本科生和研究生专业课程,组织“哲学工作坊”,并编写了多部英文专业教材,即将陆续出版发行。他们的加入不仅极大地提高了清华哲学系的国际化水平和优质哲学教育的资源配置能量,而且使得新清华哲学系的整体规模和学术教育质量都获得了空前的优化和提升。
同样可喜的是,借助清华大学“更创新、更国际、更人文”理念带来的强劲改革开放之力,特别是近两年多的清华大学人事制度改革的资源供给,新清华哲学系迎来了又一个人才引进的高峰期,仅仅在最近三年不到的时间里,我们先后从欧美名校和国内一流教研机构延揽到一大批青年才俊,如:西哲方面的蒋运鹏、范大邯、张伟特;中哲方面的陈璧生、高海波、赵金刚、袁艾;马哲方面的夏莹、陈浩等;还有一些受聘者正在向清华哲学门快步走来。仅仅就新复建的清华哲学系而言,当下的发展确乎进入了最好的发展时期,一个足以克绍老清华哲学系学统的新清华哲学学术共同体正在迅速成长壮大。
回溯20余年来清华哲学系的复建历程,作为全程经历者的我感慨良多。我清晰地记得,1999年春刚到清华上班,筹备中的哲学系仅有文南楼的两间办公室,面积不足40平米,人员不足十人。重要的不在这些,而是清华人、尤其是老清华人对母校的赤胆忠诚和不变信念。记得我刚到清华不久,张岱年先生就几次约我详谈,不仅给我讲了许多老清华哲学的故事,还向我荐举遴选中哲人才,比如,陈来兄、李存山兄和王中江兄,三位均是张先生的高足。社科院哲学所的王玖兴先生在我到清华的第一周就找我专门谈清华哲学系的复建事宜。此前,我只从熊伟先生(我硕士论文答辩委员会的主席)谈起过他和王先生一起翻译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趣事,但从未见过王先生,没有想到王先生对清华哲学系的复建如此关心。记得先生几次讲到,他一辈子只效力一所大学,所以清华哲学系被“调整”后,他没有去北大,在家“待业”多时,直到金岳霖奉命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他才应金先生之命进哲学所重新工作。因此,他一再嘱咐我“好好建设清华哲学系”,尤其是建设好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逻辑学等传统优势学科,并向我推荐过好几位西方哲学的中青年学者,其中就包括如今任教清华哲学系的黄裕生教授。哲学所的另一位老清华哲人周礼全先生更是热情,他不仅多次约我详谈,还请我吃饭。周先生念兹在兹的是如何重建和接续清华曾经开创的逻辑学学统,并先后向我推荐好几位中年逻辑学者,其中就包括如今就教于清华的王路、蔡曙山、刘奋荣诸位教授。几位老清华哲人和前辈的宝贵指导和支持让我喜出望外,同时也感到责任重大。
事实上,也正是在张岱年、王玖兴、周礼全等清华老前辈的直接指导下,我们自筹备哲学系复建事宜之初,便确立了“夯实中(哲)西(哲)马(哲)基础、突出逻辑学与伦理学特色、兼顾美学宗教科哲”的复建方案。我还想特别指出,在筹建和复建初期,直接或间接参与其间的不仅有老清华的几位先生,还有像李学勤先生(曾追随金岳霖先生学习逻辑学两年有余,后肄业于清华大学,投身于其热爱的考古学)、朱伯昆先生、钱耕森先生等老清华的哲学校友。有一件事让我深受感动和教育:清华大学90华诞(2001年四月底)期间,我遵张岱年先生和学校领导的旨意,千方百计尽最大努力邀请到全国各地尚健在的老清华哲学系的毕业生回校参加校庆,结果了解到,1952年“院系调整”前从清华哲学系毕业或肄业的老校友还有11位健在,经过努力,有十位老哲学系的校友如约回到清华园,不仅受到校院领导的亲切接见,而且张岱年先生自始至终参加了几乎全天的各项纪念活动。记得在当日上午于清华园宾馆举行的老系友座谈会上,各位前辈贤达纷纷发言,他们对母系的记忆和怀念令人感动,对刚刚复建的新清华哲学系的期待和建言让校院领导和我们这些“新来者”感到无比亲切和温暖。尤其让我感动的是,当时已是90高龄的张岱年先生不顾年迈体虚,坚持“和大家多待会儿”。座谈会进行到一半,坐在张先生身边的我发现,他似乎有些疲乏瞌睡,便悄悄地跟他说:“先生,我先开车送您回家休息吧?”未料先生精神一振,大声地说:“我今天心情精神都很好,我要跟大家多待会儿,一会儿还要跟大家一起吃中饭,为我们哲学系的重生跟大家干一杯。”先生的话,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十分感动。朱伯昆先生笑着说:“俊人,你可得好好做啊!看看张先生和我们这些老清华哲学人多支持你!”钱耕森老系友更是激情迸发,当场吟诗一首。这场景仿佛就发生在昨天,历历在目,忆之泪眼朦胧。
真诚帮助过新清华哲学系的不仅有老清华哲人,还有许多非清华的友好人士和前辈,这其中尤其让我们感动的是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哲学所资深研究员叶秀山先生。清华哲学系复建不久,我们有幸聘请到叶秀山先生作为清华大学(哲学系)的特聘教授。与时下许许多多的“特聘”“兼职”不同,叶先生的聘职工作不单是“尽职尽责”的,而且是“超职责”的。从社科院退休的叶先生几乎把他的绝大部分精力和心力都投入到了新清华哲学系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中。他不仅亲自给本科生、研究生和博士生授课,甚至亲自讲授《哲学导论》这样的哲学基础课,而且投入大量时间来培养我们的博士后和青年教师,为清华哲学系的西方哲学学科建设周密筹谋,延揽俊才,指导创办《清华西方哲学研究》辑刊,他的高足宋继杰、黄裕生、吴国盛、彭刚也在他的鼓励和支持下来到清华,其中前三位都先后加盟清华哲学团队,直到他去世前夕,还在为清华哲学系的未来发展和课程体系改进而殚尽竭力。清华哲学系的团体同仁深深感激和怀念敬爱的叶秀山先生!
新清华哲学系复建已有20年时间了,我希望新清华哲学系全体学人的经年努力和工作没有辜负张岱年先生、王玖兴先生、周礼全先生、李学勤先生、叶秀山先生和各位老清华哲学校友们的殷切期待。复建20余年来,新清华哲学系的全体同仁无分先后出处,齐心协力,为继承和弘扬老清华卓越的哲学学统竭尽了心力,应该说取得了堪慰前贤的业绩。2000年五月复建的清华哲学系,当年开始硕士研究生招生,仰仗于北大、人大、中山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山东大学等兄弟院校的大力支持,使我们最初采取的免试推荐硕士研究生招生取得极大成功,首批十来位新清华哲学研究生几乎以全优的成绩走向学界和社会。仅仅四年后,也就是2004年,清华哲学系完成了从专业本科到硕士、博士和博士后流动站的完备的学科体制重建,被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的著名教授郭湛先生赞誉为“当代中国哲学教育界的奇迹”。哲学系的复建虽然不是清华文科复建中较早的学科系,但哲学博士后流动站却是清华两个最早建立的文科类博士后流动站(另一个是2004年同年建立的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大约两年后,清华哲学系与国内诸多名校的哲学院(系)一起获准成为一级学科博士点授权单位。近年来,在学校“更人文”新战略的强力支持下,新清华哲学系的发展进入新一轮强基固本、全面提升的“快车道”,在2019年的教学评估中得到校外专家评审组的一致好评。
诚然,我们始终确信并坚持这样一种学术教育信念:最为重要的并非学科的外在性体制的优势获取,而是学科自身的内功强化和提升;同样,重要的并非诸如“学科评估排名”一类的外在竞争,而是基于国际学术和教育视野的学术资质与教育资质的自我强化与提升。为此,清华哲学系必须既有国际一流的“教哲学”(philosophical paideia)与“做哲学”(doing philosophy)的实力,又有自身的哲学学术特色和哲学教育特色。
哲学界有一种较为普遍的说法,即认为,老北大哲学系的学术特色在“史”,于中西哲学史方面名家诸多,成就非凡;而老清华哲学系的学术特色则在“论”,于哲学理论体系创建方面卓有成就,大家林立。这一说法虽不一定准确全面,但多少可以反映老北大清华两个最早的哲学系之间的学术“偏好”或特色。或许,“史论不分家”的说法更合符实际一些,在哲学史和哲学理论方面两家都有高手,也都由于后来的时势变故而有所未逮。比如说,北大的胡适先生是最早撰写《中国哲学史》的,可惜的是,不知何故,他终究只完成了半部《中国哲学史》,反倒是冯友兰先生稍后在清华执教期间完成了完整的《中国哲学史》(两卷本),并得到陈寅恪、金岳霖两先生的“审读报告”之荐,成为学界公认的《中国哲学史》的早期权威版本。
我想在此说明的是,老清华哲人的卓越成就既给我们这些新清华哲学继任者们以巨大的精神鼓舞,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学术压力。坦率地说,想要完全光复上世纪上半期清华哲学学派的气象与荣耀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不独是因为“时过境迁,风光不再”,而且也因为近世中国哲学乃是初开国门时从“无”到“有”的草创初期,少了许多“前提预制”的羁绊,多了许多“自由创始”机遇,更由于彼时的清华人文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旗帜下,大道敞开任我行的自由竞争氛围和得天独厚的“催生”条件。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老清华的哲学景象几乎是不可复制的。
然则,不可复制绝不意味着无所作为。身为桃花源中人,很自然我确实难以对如今的清华哲学系做出客观清晰的学术评估,正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过,作为亲历者和参与者,我还是可以谈一点自我感受的。我以为,新的清华哲学系至少已经具备一个好的学术共同体的基本要素:好的学术传统,好的团队,好的学术带头人,好的学术团队氛围,好的学术工作方式,以及,由此所创造的好的学术发展潜力和前景。关于好的学术传统前面已经多有备述,无需赘言再三了。
关于好的学术团队等方面,我可以坦诚地说,入职清华的头一年,我用心最多的问题是,究竟复建一个怎样的清华哲学系?感谢学校给我提供了自由考察国内外多所名校哲学系的机会,通过仔细考察欧美近20所著名高校的哲学系和国内多所兄弟高校的哲学系,我们在复建之初便确定了“有所为有所不为”、“不求面面诸到,但求有无相生”的建系原则。因之,我们所采取的方式是“先找方丈后找和尚”,其不便明说的理据是“山不在高,有仙则灵”。也就是先找好哲学各二级学科的学科带头人,然后再配置青年才俊,以成学科梯队。在哲学的八个二级学科中,我们把中西马(哲)视作哲学一级学科的“三驾马车”和“基础型学科”,务求夯实垫高;逻辑学是清华的老传统且具有原创奠基的历史地位,故必须优先发展;伦理学和政治哲学被国内外绝大多数名校哲学系看作是当代和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哲学学科能够“老树发新枝”的主要生长点,故需要集中优势资源优先发展。其他诸如科技哲学,我们选择联合当时的科技所(即现在的科学史系)攀援而上的策略;而美学和宗教哲学则力求精致与特色,这就是为什么如今的清华哲学系的美学专业侧重于中国美学和中西美学比较、宗教专业则选择以本土佛教、景教和域外东正教、基督教以及中外宗教哲学比较的主要缘故之所在。
应该说,我们的设想和目标已然初步达成,有些甚或超乎预期,比如,我们在学校强有力的鼓励和支持下所创设的三个哲学讲席(团),我们在中哲、西哲和马克思文献研究、逻辑学、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的教学研究成效,基本上也确证了这一点。更值得宽慰的是,新生的清华哲学系已然形成了良好的学术氛围和开放前沿的学术工作与学术合作方式:学术独立而学人团结互助;学术自由而团体公正有序;坚持学生优先、学术优先、学者优先(教授治系);继承并弘扬清华哲学学统而又紧接国际哲学界前沿;中外兼容、老少咸宜;一个“小而精”的“哲学特战队”式的学术共同体蔚然形成,沉静从容而又充满生机。这正是我们一直孜孜以求的!
本《文集》汇集了哲学系十几位教师具有专业代表性的论文,《文集》的编辑原则是自愿入选,有些同仁因为某些原因没有选择陈文,而是选择单独集文出版或者贡献学术专著,有些同仁则是因为考虑到刚加入清华哲学系不久,不想以曾经在其他工作单位发表的论文入选其中。我们尊重各位同仁的自主选择,也把这种“单位文集”选编的方式,看作是一种用以展示学科之学术团队的阶段性成果的初步尝试,并期待在以后编集得更全面更完整一些。但即便就目前这部《文集》来看,已然较为清晰完整地展现了新清华哲学系作为一个学术共同体的基本学术面貌,细心的读者和方家从中不难见出我们这个学术群体“做哲学”的工作方式和学术路径。我们当然特别期待国内外哲学同仁的批评和指正,更希望以此作为我们的一份学术邀请函,欢迎校内外专家同仁、特别是清华校友们加入我们的“哲学游戏”,俾使更多的人在更多的时候和场合习惯于以哲学的方式思想和行动。作为古希腊文明的两大发明(哲学与奥林匹克运动会)之一,哲学曾经且一直都是西方文明、特别是西方近现代文明演进的重要文化资源和精神动力之一种,一如道德伦理曾经且一直都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精神资源一样。无论如何,以“爱智慧”来自我标榜的哲学都是一门有益于人类自身及其社会进步的论理方式和思想学问,在“创新”日趋凸显的现时代,人们对智慧的偏爱和追求无疑也会与日俱增,就此而言,哲学的时代非但远未“终结”,反而重新“来临”!
谨代表清华哲学系全体同仁,以此《文集》作为清华大学110周年华诞的一份学术献礼,以及,作为我们对海内外哲学同仁和一切热爱哲学的人们的一份“问道为学”的邀请函!
且为序,所望焉!
农历庚子初春新冠疫情期急就于京郊悠斋。
[1] Cf. Junren, WAN, ACharacterization of Philosophical Knowledge in“Chinese Modernity”, In: European Review, Vol. 11, No. 2, [2003])。(参见万俊人:“中国现代性”中的哲学知识刻画,原载《欧洲评论》,2003年,第11卷,第二期)。
[2]参见拙文:“学统,知识谱系和思想创造”,原载《读书》杂志,2002年第八期。(后收录于拙著《正义为何如此脆弱——悠斋书评及其他》,河北石家庄:河北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3]张申府:“哲学系概况”,原载《清华周刊》第41卷,1934年6月1日。转引自《清华大学资料选编》第二卷(上),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26页。
[4]以上史料和议论均取自《清华大学文史哲谱系》一书,万俊人主编,刘石、王中江、彭刚副主编,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我为该书所撰之序“大学的学统与人文知识谱系”亦可资参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