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中国哲学史”正名
我要讲的学科是“中国哲学史”,先简单地对这个学科进行一下“正名”。其实在教育部现在颁布的学科目录中,我们这个学科名称叫“中国哲学”,类似的有“西方哲学”。而在二十年以前,这个学科名字叫“中国哲学史”,相应地“西方哲学”叫“西方哲学史”或者“外国哲学史”。但是目前教育部这个目录名称也有它的理由,这个名称的涵盖会更宽一些,它不限于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还包括对中国哲学体系本身的研究和发展。但是为什么我们还要强调将“中国哲学史”作为这个学科的基础特点呢?因为我们认为在大学哲学系从事“中国哲学”专业的学习和研究,主要就是在做“中国哲学史”的学习和研究。所以从本科生到硕士生乃至到博士生的学习阶段,我们的学习研究都是紧紧扣住“中国哲学史”这个学科名义来进行的,换句话说,在这个学习阶段,我们不是鼓励大家做中国哲学体系的创造研究,而是强调哲学史的基础学习和研究。哲学创造的工作是大家将来毕业以后有条件时再来进行的一种研究,如果说写博士论文就要发展一个哲学体系,这个是我们不鼓励不建议的。事实上在国外大学哲学系,对博士生的培养也是一样。博士毕业以后有的是时间来做体系性创造性工作,目前最重要的是打好哲学史基础。所以我常讲我们这个学科的初心就是“中国哲学史”。现在全国有很多中国哲学硕士点、博士点,基本的培养方式就是学习怎么做“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今天我们这个学科在大学学位培养的环节当中还是要以“中国哲学史”为主。虽然现在这个学科的名称是叫“中国哲学”,但并不是让学生现在就离开哲学史独立地创造自己的哲学体系,这并不是我们的目标。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在中文系你进来了不是让你作一个独立创作的作家,而是培养你的文学素养,包括对文学史、文学理论甚至文献文字的学习。目前我们国内绝大部分中国哲学硕士点、博士点都是用这种模式培养学生的,此外只有很少的、个别的学校可能没有强调这个学科特点,这样学生就不能足够地关注学科史的训练,而过早地去涉及自己体系的创造,结果最后大多数都不成功。所以我们强调哲学要有训练,训练最主要的就是哲学史的训练。以上就是首先讲的正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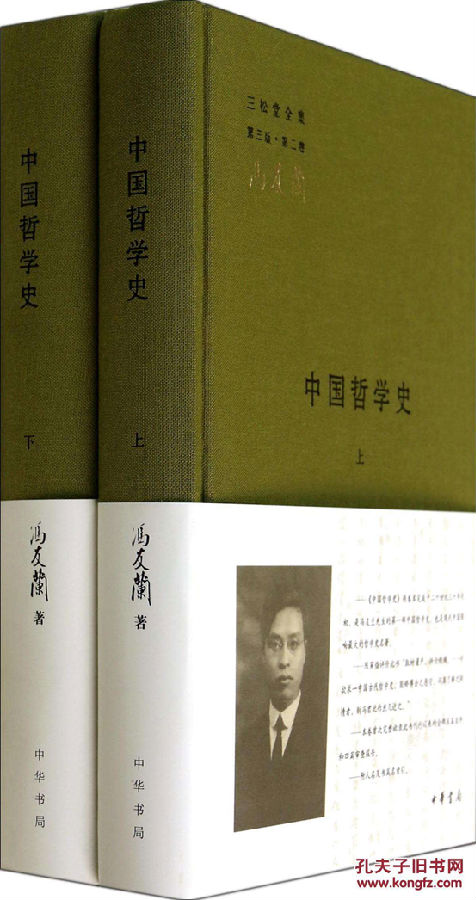
二、学科的发生与发展
再讲“中国哲学史”学科的性质和历史。
“中国哲学史”这个学科本质上是东亚文明和东亚国家在教育和文化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个学科。在东亚文明历史上本来并没有这样一个独立的学科。“哲学”这个概念本身来自日本哲学家西周对philosophy的翻译,在此之前中国人也翻译过其他名字。因此中国哲学史是近代以来东亚国家学者参照比照西方(欧洲)学科的名义、体系来建构的,即参考欧洲哲学概念、欧洲哲学历史来建构中国文化中有关理论思维的发展历史。
“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出现首先在日本。日本是在1840到1850年代被迫走上近代化的历程,但是日本走的步伐比较快,而中国国家大、历史久,“大船”调头要稍微慢一些。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二十多年,大概在1890年前后开始出现“中国哲学史”这个学科。用日本人的文字表述就是“支那哲学史”。据研究最早在1888年有一个叫内田周平的人写了一本《支那哲学史》,但是这个《支那哲学史》写得不太成功,只讲了先秦诸子,而且都是老的讲法。这说明在日本学科建立之初也是先确立了“哲学”作为近代化学科的重要性,然后在这个学科概念里面尝试把东亚文化重述出来。在1898年以后东京大学才出版了松本文三郎的《支那哲学史》,其特点就是不只讲先秦了,而是开始有“分期”的观念了,他称中国哲学史各分期为“创作的时代”“训诂的时代”“扩张的时代”。“创作的时代”主要指先秦,“训诂的时代”主要指汉唐,“扩张的时代”就是宋代以后。在他的研究框架中佛教还没放进去,但他的分期研究方法是一种进步。到1900年,远藤隆吉也写了《支那哲学史》,他在分析表达上有了进步,他用了很多和后世比较接近的讲法,比如在哲学思想内容的分类上开始使用“宇宙论”“伦理学”“工夫论”“心性论”。我国的中国哲学史教材当中,从五四以后一直到八十年代都没有用“工夫论”这个概念,大致在新世纪以后,有些教材才开始用这个概念。当然在学术研究领域运用“工夫论”这个概念比较多见了,尤其最近二十年。远藤隆吉在中国哲学内容的分类方面除了用“宇宙论”“伦理学”等现成的西方哲学概念外,他还用了“心性论”“工夫论”这些类别的设定,所以说他又比以前更进一步。整个日本的“支那哲学史”系统要到1910年才比较成熟。1910年高濑武次郎写了《支那哲学史》,其中在分期上有了新的提法,即“上世”“中世”“近世”。后来中国学者会有另外的表达,比如“上世”说成“上古”,“中世”说成“中古”,“近世”说成“近古”。总而言之,高濑武次郎这个分期对日本和中国影响都比较大。此外他对哲学内容的把握和叙述也有新意。刚才我们讲远藤隆吉用了“工夫论”的概念,高濑武次郎也有个发明,即使用了“气一元论”这个概念。我们过去讲气的形态、气的思想时,特别是在讲张载的哲学体系时,会用“气一元论”这个概念,这个其实就是高濑武次郎所使用的。所以“中国哲学史”的出现实际上是在反映整个东亚文明从古代到近代的一种进步,是一个新的学科的设立。
回到中国,“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立同样经历了一个过程,即其初期主要通过建立中国哲学史课程和写作《中国哲学史》教科书来实现学科的发展。1898年,京师大学堂建立。其中与中国哲学史有关的,是1906年王国维写的《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这篇文章针对的主要是张之洞,张之洞等人认为哲学没有什么作用,所以他们管理的京师大学堂并没有哲学学科,只有经学学科。而这是王国维不能满意的。王国维强调哲学学科的重要性,于是就按自己的理解设立了这个学科的课程:第一是哲学概论,第二是中国哲学史,第三是西洋哲学史,另外还有一些其它课程。关于“哲学概论”,王国维自己翻译过一本日本人写的《哲学概论》,所以他对这个课程的体系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在他对京师大学堂哲学学科的设计规划中,排在第二位的是“中国哲学史”。而不管是设立哲学概论,还是中国哲学史,都是吸取了邻邦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学术近代化、教育近代化的经验之后提出的建议。王国维的这篇文章是具有学科意义的。日本1890年后二十年的发展也和这个情况类似,大多数写“支那哲学史”的,都跟东京大学有关系。
中国的第一部《中国哲学史》出现于1916年。但其实在这之前,1914年-1915年北京大学就已经开设了“中国哲学史”课程。1915年,冯友兰先生入校学习中国哲学史,当时讲课的老师是陈黻宸,浙江永嘉人。由于学生听不懂方言,又没有现成的教科书,所以陈先生就把讲义写好,再发给学生。他最后一次讲完之后,向学生说了一番话,虽然同学们听不太懂,但能感受到陈先生的诚恳,所以心里都很感动。陈先生教完冯友兰先生这一班之后第二年就去世了。
1916年,坊间出版了四川学者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谢无量比冯先生大十岁左右。他其实并没有在大学教书,但他写了《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说明他对当时教育的近代化非常关切。虽然个别地方有所补充,但就体系、框架、分期而言,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基本上还是对1910年高濑武次郎《支那哲学史》的沿袭。我们今天同当时人有一点很不一样,就是过分强调知识产权的私有性,反而忽视了文化传播的积极性、公共性。其实近代的很多学者(如谢无量),当时都参考过日本学者的新研究。其中一个原因是,中国与日本在文化上有许多相似处。在日本文化的近代化过程中,除了自身的特色(如神道教)外,还有很大一部分是自中国而来、在日本也流行的文化思想、文献,这些东西构成了日本知识人的教养,构成了他们知识人的古典基础。此外,日本的近代化发展比中国早了二十多年,他们先走了这一步,所以中国学者就跟着学习,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中国要学习一些先进的东西,日本学者走在我们前面,向他们学习,这样可以省去一些从头再来的功夫。谢无量这本书的产生亦是如此。当时中国还出现了好几种日本关于中国哲学史的译本,包括高濑武次郎以及后来比较有名的宇野哲人、武内义雄等人的著作。宇野哲人的《中国哲学概论》,武内义雄的《中国哲学思想史》,还有渡边秀方的《中国哲学史概论》。这些书原先都叫“支那哲学史”,翻译之后就叫“中国哲学史”。
谢无量这本书适应了当时教育近代化的一种需要。但这只是一个初步的工作,还不能代表中国人对中国哲学史学科建立的基本贡献。1917年,胡适来到北大,1918年开始开设《中国哲学史》课程,1919年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这本书是中国的中国哲学史发展过程中具备里程碑意义的第一本书。它的主体内容是胡适在美国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名学”就是逻辑),然后再加上他回国以后的讲义,补充了一些历史考证。当时傅斯年、顾颉刚都去听过胡适的课。他们比胡适小不了几岁,旧学的根底也不比胡适差,但他们对胡适都是很信服的,都强调胡适的课讲得不错,有新的见解。所以胡适就成了青年导师。高濑武次郎曾把他的支那哲学史寄给杜威,后来杜威来中国期间,把胡适此书赠送高濑武次郎,高濑武次郎也认为胡适此书“其所论亦不少崭新奇拔之处”。
但是胡适这本书只有上卷,只写了先秦,因而并不完整。直至十几年后,才出现了第二个中国哲学史学科的里程碑意义的著作,那就是冯友兰先生在1930年代初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两卷本。它最早在神州国光社出版了上卷,后来上下两卷收入清华丛书。在内容上,它不限于先秦,而是一直写到清代,是一部完整的中国哲学史。收入清华丛书时,它经过了金岳霖、陈寅恪两位先生的审查,这是大家都熟知的。在金岳霖和陈寅恪的报告中,都把冯先生的书和胡适的书作了对比,他们的共同结论就是冯先生的书要好过胡适先生的书,“好”不只是内容上的全和不全,而是在哲学史的方法和态度上也不一样。金先生对胡适的批评还是很尖锐的,他认为胡适写哲学史的态度就像美国商人一样。陈寅恪的主张是对古代哲学家要有了解的同情,这是做一个好的哲学史家的基本条件。冯先生的书很明显的优点之一是他对什么是哲学史这一观念做了很详细的检讨,在方法论上有明显的自觉。中国哲学史这一领域他有很多的分析。在很多地方,他引进欧洲哲学的一些内容进行比较,通过进行比较来说明和增进对于中国哲学和哲学家思想的了解。于是冯先生的这两卷中国哲学史就取代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胡适上卷写完后一辈子都没有心情再写了,因为胡适到30年代就开始反哲学了。他在北大当文学院院长,碰到北大哲学系老师,说话都是反哲学的口气,他自己也再没有写《中国哲学史》的中卷与下卷,他转移到“中国思想史”的研究道路。冯先生此书1952年就出了英译本,是由卜德翻译的。同时因为冯先生1947年到1948年在宾夕法尼亚教中国哲学史这门课,写了一个英文的讲义,在当时译成英文出版,80年代才由冯先生的老学生涂又光把它翻译回来,叫《中国哲学简史》,是1985年北大第一次用电子的激光排版出的一本书。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二卷本,一直以来在国内国外有着很高的声誉。在西方,至今没有出现能够取代它的一本新的《中国哲学史》。当然原因很多,但也可以看出冯先生的工作也是受到大家重视的。后来冯先生不断改写,晚年改写成《中国哲学史新编》。但是《中国哲学史新编》并没有大学把它作为一本教材,冯先生两卷本的30年代的《中国哲学史》,在三四十年代是大学普遍作为“中国哲学史”这门课的教材,对学科的影响力极大。冯先生写的这两本书,是冯先生在清华教课的用的,所以我们清华的教材和教学是结合为一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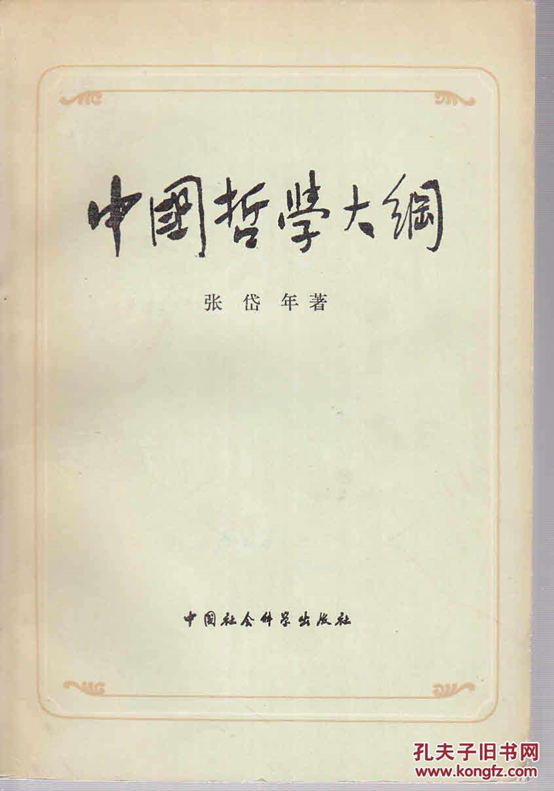
张岱年先生1933年来清华教书,1936年就完成了《中国哲学大纲》这部著作。张先生当时也是用《中国哲学大纲》讲稿在清华教书的,冯先生的两卷本是中国哲学史的通史,而张先生的书不是按通史写的,他是按照问题和体系写的。所以一个是纵向的,一个是横向的。30年代清华的中国哲学学科很明显从教学到教材到课程,应该说在国内都是领先的。可以看出,清华前辈的这两本著作,使得当时清华中国哲学的学科名列前茅。
关于题为“中国哲学史”的著作可以再补充一点,在胡适的书出版10年以后,在冯先生的书还没出版的时候,1929年,钟泰出版了一本《中国哲学史》,此书在后来的哲学史的发展中被淹没。因为胡适很有名,所以书的影响力很大。等到冯先生的两本《中国哲学史》出版后,就取代胡适的地位,大家都接受了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体系。钟泰出版的《中国哲学史》特点是什么呢?应该说这本书体系的特点,依然是贴着高濑武次郎的《中国哲学史》来的,跟谢无量的书比较接近。但同时他有一个特点,跟胡适、冯先生不一样,就是他始终要避免使用西洋哲学的概念来比较、分析、说明、认识、理解中国古代哲学思想。而十几前年重印此书,跟当时的一场讨论有关,当时有一些学者批评在研究中国哲学时“以西释中”,于是就翻印这本书,但是影响不大。不仅“中国哲学史”这个学科本身是近代化的过程中学习西方近代化建设而产生的,同时学习西洋哲学更是这个过程内在的部分。冯先生、张先生都非常强调要研究好中国哲学,一定要学好西洋哲学。
以上是关于学科在解放前发展的基本情况。在解放之后,学科有了一些新的做法,主要就是由教育部统编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教材,从60年代到80年代都这样。最早是由任继愈先生主编,联合在京各个单位,北大、中央党校、人大、学部哲学所的学者,写出四卷本《中国哲学史》,文革前完成三本,后来文革中又写出一本。这就相当于部颁教材,教育部组织学者来写,其中以北大学者为主。到了文革以后,教育部又重新支持教材建设,支持北京大学修改在文革中编写的《中国哲学史》,后来由中华书局出版。后来又支持南方武大和中大的老师编写教材《中国哲学史》。从这以后,部颁教材的写法组织也少了,很多大学哲学系自己来写自己的中国哲学教材。事实上,是否需要每个学校都要写一套自己的中国哲学史教材,我倒不觉得该是这样。但是很明显,每个学校的课程,老师在讲时肯定要结合自己的体会,有他认知的重点,有他喜欢的讲解方式,所以讲课肯定就变得多元化。现在有好多的教材,南开大学、复旦大学等很多大学都有自己的教材。所以,从学科来讲,教材在现在不是发愁没有,而是如何在众多教材中进行选择。也有一些学者个人来写中国哲学史,比如武汉大学的郭齐勇教授,自己也写了《中国哲学史》。这都是我们新时期以来教材的多元化发展。当然每个时代不一样,到80年代写的教材就比60年代写的教材在思想观念上更进步。“更进步”就是说去掉60年代禁锢大家的一些教条主义的观念,在“解放思想”的口号下,更自由地做中国哲学的研究。包括到90年代以后,有很多个人写的《中国哲学史》不仅吸收了国内相关教材的写法,也吸收了很多海外相关的观念和写法。
从文化中国的角度来看,中国哲学这个学科,不仅要看中国大陆哲学系的教材,如果放眼台湾、香港、澳门,他们哲学系的教学同样也有学科和教材建设的问题。但是这个教材的建设成就是比较单一的。香港台湾得到大家较高评价的是劳思光的《新编中国哲学史》。他从1968年开始写,第一本书叫《中国哲学史》,第二本还叫《中国哲学史》,到第三本上册出的时候,还是叫《中国哲学史》。但后来他的写法有些改变,他不想把它仅仅作为教材,就改叫《新编中国哲学史》,到八几年才完全完成。这套书是在海外、在香港、台湾得到了比较好的评价的中国哲学史著作。我们不能够详细地在此评论这本书,关于此书我只想讲一点,因为劳思光是北大哲学系的学生,他是四七年前后进入北大哲学系念书的,没有念完就到了台湾、香港。我看他的书有一个感觉,就是他的讲法比较接近于北大的学风,这跟其他的新儒家论点不太一样。如果讲到这个学科的教科书建设,劳思光的这个书应该说也有它的地位,我们可以来参考。如果不仅作为大学教科书,那么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前四卷,应该说其水平超过了其他几种《中国哲学史》教科书,更值得重视。
“中国哲学”学科内容很广,这里为简单起见,以写“中国哲学史”通史教材为中心做一个描述。这是我讲的第二个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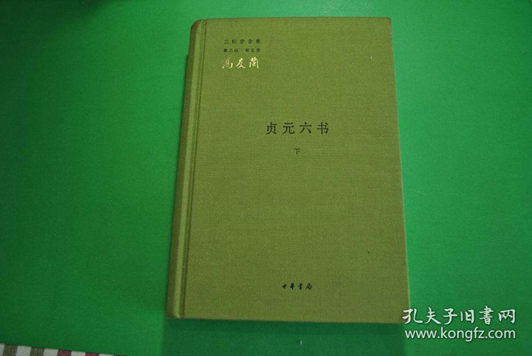
三、哲学史与哲学观
第三点要讲的是中国哲学史百年来撰写过程中的哲学观的问题。
胡适在他的书里讲了一点对中国哲学的理解,冯先生在他的哲学史的上卷一开始就讲得很详细。冯先生当时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哲学是西洋概念,现在讲“中国哲学史”就是在中国学问中,来看看哪些可以用西方哲学的名词来概括它,可以算在西洋的哲学的名词内,就把它挑出来叙述。冯先生大体上做了这样一个工作。当然冯先生也有一个结论,就是说中国古代的像魏晋的玄学、宋明的理学、清朝人所讲的义理之学,它的研究内容对象约略与西洋哲学相当,这是冯先生当时对哲学和中国哲学史的讲法。当然冯先生也说,我们有两个学术选择。因为中国文化不同,可能有一个中国自己的义理之学的体系,就是西洋的哲学如果用中国人的讲法来讲就是一种“义理之学”。如果这样看待,现在讲中国哲学史,一种是前面讲的严格地按照西方所谓的哲学的内容去找古代的那些相关的思想资料素材;另一种写法是以中国自己的义理之学的体系本身,成体系地来论述义理学史。冯先生选择的还是前者,就是用西洋的哲学的名义来看,来取材,看看中国的文化里面与之相当者;但这不是绝对的,在这个前提下,还要顾及中国义理学体系的某些内容和特点。这是冯先生当时的关于哲学史的想法。在三十年代中期张岱年先生写《中国哲学大纲》的时候就重新讨论这个问题。张先生讨论这个问题,认为这个问题也很难解决,西洋哲学家对哲学的了解也是一家一义、一家一说,从而就变成一家之言,也没有说就有一个一般的“哲学”观念的解说。当然如果从各家的哲学观加以抽象、加以总结,可以说哲学是讨论宇宙、人生的究极原理以及认识此种原理的方法的学问。张先生当时是这样看的,看来中国古人所讲的那些义理学的形态里没有跟这些西洋的哲学是完全相同的,但是他的确同意冯先生的话,认为玄学、理学等约略相当于现在所讲的哲学。但是在中国清代以前的确没有一个总名能概括了诸子之学、玄学、理学这样一个一般的名称。张先生说把现今的诸子学、魏晋的玄学、宋明的理学、清代的义理学合起来,是不是可以称为中国的哲学呢?这要看我们对哲学这个词怎么定义。如果你了解的哲学的定义是专指西方哲学那个类型的学问,认为西洋哲学才是哲学所以为哲学的唯一的标准,那因为中国哲学在态度、在体系等方面与之不一样,就很难叫“哲学”了。但张先生自己的主张是这样,他说我们可以把哲学看做一个类型,而不是专指西洋哲学形态的那种体系。在这个类型里边,在这一类的学问里边,西洋哲学是其中的一个特例。这个学问的总名叫哲学,可是西洋哲学是这个总名里面的一个特例。那么跟这个西洋哲学有相似点的、可以归为此类的也都可以叫“哲学”,比如说中国古代关于宇宙人生的思想,印度古代关于宇宙人生的那些思想,都是这个总名下的特例,都可以称为“哲学”。这是张先生当时在《中国哲学大纲》里面所主张的一种哲学观。张先生的讲法是富有启发的,应该把哲学看做一个“共相”,应该把它作为一个“家族相似”的概念,在这个下面西方欧洲人关于宇宙人生的理论思考,印度人关于宇宙人生的理论思考,中国古人关于宇宙人生的理论思考,就构成了西方哲学、印度哲学、中国哲学。而哲学应该是世界各个文明系统里面对宇宙人生理论思考的共相。而西方哲学也好,中国哲学也好,印度哲学也好,都是哲学的殊相,跟共相相对的,是一个例子,而不是哲学所以为哲学的标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哲学这个概念不应该被认定为西方传统的特殊意义上的东西,而应该是世界多元文化里边一个富于包容性的普遍概念。这是我们今天认识哲学概念的哲学观。所以中国的义理之学应该说就是中国哲学,当然它的范围,包括一些特点跟西洋哲学有所不同,它关注的问题和西方哲学的问题也有所不同,这并不妨碍它成为中国的哲学,而这恰恰体现了哲学就是共相和殊相的统一。因此,在世界多元文化发展的今天,非西方的哲学家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发展起一种广义的哲学观念。在世界范围内推广,要解构西方中心的立场,这样才能真正促进跨文化的哲学对话,发展二十一世纪的人类智慧。如果未来的哲学理解,仍然是受制于欧洲传统,或者更狭小的英美分析的传统,那么哲学的人文智慧和价值导向就很难体现,二十一世纪人类的前途也不会比上一个世纪更美好。这种说法并不意味着不要学习西方哲学,因为从历史的现实来看,西方哲学是人类智慧中理性分析和建构的代表,西方哲学的形态虽然是“特殊”,但是其中不少问题的讨论是具有普遍性的。西方哲学的哲学论述虽然不是哲学所以为哲学的根本规定,但是学习西方哲学可以为研究其他哲学提供具有普遍意义的重要研究方法和参考视野。特别是西方近代以来的哲学,虽然它仍然内在于西方语言的限制,可是伴随着人类的历史走向世界史,其中的讨论,地方性的局限渐渐减少,与科学和工业文明发展的普遍性的连接越来越多。所以,今天讲学习中国哲学,以前冯先生、张先生都讲过,学习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方法是要学好西方哲学。与这个问题相关的再提一句,就是宗教研究。应该说,一两百年以来世界宗教的研究显示出“宗教”这个概念的定义,与西方早期的意义相比已经渐趋宽泛,容纳了西方以外很多的经验,所以显示出宗教研究和它的基本观念在相当程度上摆脱了西方经验的局限,而注重宗教现象的多样性。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宗教研究比哲学研究要更为进步。其实从整个世界文化史几百年的发展来看,近代以来世界文化的发展可以说就是以西方文化为普遍标准到日益吸收非西方世界经验而不断将原有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加以扩大的过程。今天还用的这个“宗教”的概念已经大大不同于西方基督宗教经验的那个意义。所以宗教是这样的,哲学也应该是这样。这就是哲学观的问题。当然这类问题的争论,在短期内并不会结束,但是随着世界交往的扩大,随着西方中心主义的逐渐解构,随着在世界范围内多元文化主义的影响日益深入,包括西方哲学内部所谓“哲学的终结”这样的说法引起的反思的深入,终究会大大改变我们对这类问题的认识。这是第三点,关于中国哲学史写作里面涉及的哲学观的问题。

(张岱年先生)
四、学习中国哲学史的方法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学习中国哲学史的方法。
首先来简单说一下冯友兰先生关于“照着讲”和“接着讲”对比的提法。冯先生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就提了这个问题,当时他主要是用来区别哲学史的工作和哲学创造工作,即哲学史的重点是要说明以前的人对某一个哲学问题是怎么说的,哲学史就要把这个说清楚:他到底怎么说的。不能人家说的是西,你在讲的时候说成是东,这就不是“照着讲”。所以哲学史一定是要“照着讲”,说一就是一,说东就是东,前人对问题是怎么说的,要尽量要把他言说的状态重新表达出来。而“哲学的创造”是要说明一个哲学家自己对这个哲学问题怎么想。但是由于每个哲学家在思考哲学问题的时候总是要以前人怎么说的作为思想材料,所以就是“接着讲”:一方面接续着前人的哲学思考,一方面有所发展、有所不一样。这就是冯先生在新理学里面讲的“接着讲”。所以冯先生这两个概念本来就是来分别哲学史和哲学,对于哲学史研究和哲学研究的工作方式做了一个区别。
可是冯先生这个讲法,如果不善解的话也会引起一种不恰当的理解,就是认为哲学史研究没有什么创新可言,只有哲学理论的创造才有创新可言。其实不是这样,因为每一个研究者的主观前见是不一样的,而且这个主观前见是不可避免的,人的理解能力,特别是理解古人哲学思考的能力不同,加上古今语言的表达的隔阂以及人的哲学的修养不一样,所以每个哲学史家的理解、成见往往是不相同,而这个不同的水平差异是有客观的标准可以衡量,不是不可知的、不能衡量的。而且哲学史的研究不仅要对历史上的单个哲学家进行研究,还要说明不同的体系之间、不同的时代之间的哲学的“古今之变”和种种复杂关系,那么这些都需要比较细密的分析能力、比较高度的理解能力、比较全面的观察力。从这样一个比较积极的角度来看,哲学史的研究就不是一般人理解的“照镜子”那么简单,所以哲学史的研究领域也是充满了能动的创新的可能和需求,充满了研究中这种创新的智力竞争。因为哲学史的创新之所以有可能更困难,因为它是有对象可以检验。哲学史有现成的文献,有众多的研究,这和自己独创一个体系,无从检验,那还是不一样的。
而且哲学史的研究也要“接着讲”,只是不是对每个人、历史上某一个哲学体系去接着讲,是要接着前人对同一对象的研究成果继续深入,接着前人的研究基础,要全面的了解前人的研究成果,才能加以创新。所以哲学史上的创新跟哲学上的创新是有同样的困难,如果不是更困难的话。
这样“接着讲”的意义也是很重要的,就是它的意义不限于哲学。其实一切人文研究都应该采取“接着讲”的态度和方法,“接着讲”就是传承创新。创新要有所本,有它的基础,接续前辈学者和同时代已有成果,“据本开新”,发人之所未发,要比前人有所创造、有所前进。这样学术发现、学术创造就能走上一个良性增长的大道。所以冯先生的讲法从广义上来讲有很多可以发明的地方。
那么仅就“照着讲”本身来讲,它作为哲学史的工作方式的特点,有它自己的需要强调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张岱年先生反复提的,我叫做八字真经,即“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这原是太史公的话,太史公的原话是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张先生就抽出了“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这八个字来强调这个中国哲学史研究学习的根本的方法和态度。冯先生也讲过同样的意思。这应该是过去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哲学史学科共同强调的、主流的研究方法。张先生讲过,“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应该是哲学史家的座右铭。所以研究中国哲学史应该特别强调的就是对文献的正确的解读,这是最基本的。“好学深思,心知其意”的对象指的就是中国哲学史上要研究的这些基本文献(就是每个哲学家的著作,著作当然有不同的形式,包括语录等等)。所以“好学深思,心知其意”的“其”是针对这些文献来讲的。理解不能出差错,虽然差错是难免的,但是要通过学习来减少这些差错。类似出差错的例子,张先生其实讲过。如老子讲“道之为物”,“为”是作为的意思,有些人将“为”解释为“创造”,就把“道之为物”在根本上解释错了。当然,有些命题有多重含义,但在语言学上犯基本错误,是在研究哲学史上应避免的。哲学史工作的严谨,首先就是文献解读的严谨。清人讲学问有义理、考据、词章,做哲学的“词章”之学要体现在对文本的正确把握,不能把文本解读错。哲学史课程的重点是读文献,帮助大家打好基本功,不能在文献上出错,这非常重要,这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中国哲学史的课程不是教大家结论,而是练习解读文献的内功。
其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还包括一些重要方法,如学好中国哲学要注重外国哲学,但不能生硬的将外国哲学的概念移用到中国哲学上。“心知其意”是要反复的体贴、体会中国哲学概念的准确意涵。老先生曾举过不少例子。如张先生讲过,西方哲学有些概念用到中国哲学概念要小心,如关于理学的“理”是什么含义,有些学者解读为“精神”,这是不对的,要对中西哲学概念的细微差别加以把握。“理”解释为“观念”还可接受,但理“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不能理解为“精神”。此外中国哲学有些概念,和我们用来翻译西方哲学的一些概念,用的词是一样的,可是其内涵往往不一样。“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要求我们不能够望文生义。如张载讲“太虚无形,气之本体”,这个“本体”的意义是什么呢?有的人直接把它用西方哲学的“本体”概念来讲,那就不能理解张载哲学的本意了,“气之本体”这个“本体”是讲气的本来状态。“本体”是中国哲学的固有名词,但“本体”的意义有多种用法。
总之“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是中国哲学史研究最重要的方法。要求我们对古代文献正确的解读,不能望文生义。要求我们学好西方哲学,但是用西方哲学来比照分析中国哲学概念的时候,要特别谨慎的加以区别。这两点是我们的前辈老师特别注重的。
结语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清华已经是中国哲学学科发展最重要的大学。本来北大起步早,但因为胡适在二十年代末就开始反哲学,他对北大哲学系的建设是不用心的,同样他自己的《中国哲学史》也没有进行下去,因为他根本就反对哲学的概念。从三十年代初开始,以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上卷出版为标志,包括张先生在清华写了《中国哲学大纲》,并且用来教学,标志着清华当时在中国哲学学科方面,不仅做出了划时代的里程碑式的贡献,而且从整个学科的教学、体系、教材来讲,应该说走在整个全国的前面。到了西南联大时期,胡适因为长期在美国,所以西南联大的文学院是冯先生领导的,哲学系里面中国哲学史也是由冯先生讲的,西南联大的中国哲学学科虽然是三校在一起,但应该说冯先生的学术思想还是起了重要的引导作用。解放以后,清华的哲学系全部并入到北大,全国很多大学的哲学系老师都并到了北大,而解放以后的北大的中国哲学史学科发展,主要还是由冯先生引导的。尽管冯先生也受到了很多的批判,但总体来讲,北大的中国哲学史学科,是由冯友兰先生、张岱年先生、朱伯崑先生三个老清华的先生主导的。因为汤用彤先生解放以后做北大副校长,承担很多行政工作,而1954年因为脑溢血中风了,也影响后来的工作。当时教研室是冯先生做主任,中哲学科的工作应该说还是受到冯先生的影响最大,而张岱年先生和冯先生关于中国哲学史的学术思想是一致的。1977、78年改革开放以后,北大中国哲学学科的发展主要受张先生的影响。张先生80年代中期退休,在这前后朱伯崑先生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朱先生也是老清华的。以前我们78年当研究生入学的时候,问张先生,朱老师是不是您学生?张先生说:“是啊,他上我的“中国哲学史”,两个学期我都给他一百分。”朱先生也是清华的中国哲学史学科训练出来的,又长期在北大协助冯先生写《中国哲学史新编》。所以解放以后,北大的中国哲学学科居全国之首,但是它的中国哲学学科的建设,始终贯穿着清华学派的贡献,清华学派的学风在中国哲学研究方面,融进北大而且成为北大中国哲学学科的主导的力量。所以今天不管在北大还是在清华,我们有共同的祖师爷,要发扬这个精神,要把冯先生、张先生开创的中国哲学科学,他们奠定的这个学科的基本的学风,继续下去,不断加以发展。
(本文是陈来先生2020年9月1日在清华大学哲学系研究生新生入学引导讲座上的讲话整理稿,已经陈先生改定。感谢孔维鑫、黄永其、任艳、王泽婷、王慧聪、王铁桩几位同学的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