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研中华文化 阐扬传统专学
探究学术真知 重视人文关怀
中国文化 2020年春季号
[题头]本期《中国文化》刊载黄裕生教授文章,对“世界上只有中华文明是唯一延续不断的”说法,提出讨论,认为一种文明的延续性主要不在于其语言与民族性保持简单的自我同一性,而在于把人类或族群的存在带上能够进行不断自我突破、自我提升的跃动轨道。
如何理解文明的延续与中断
——从一个说法谈起
黄裕生
在我们的学界与民众的观念里,一直很流行一个说法:世界上只有中华文明是唯一延续不断的。这越来越成了人们获得文化自豪感与优越感的一道符咒。但是,要使这道符咒持续有效,有必要认真追究一下这一说法的可靠性,以便澄清,在这令人骄傲的绵延中,究竟是延续了什么伟大的东西,而竟不是延续了没有突破的停滞?如果它的确延续了某种伟大的东西,其他文明与文化是否也有这种延续呢?只有能经受这些追问,这一说法也才可能得到世界其他文明实体的认同,而不只是一道自我迷幻的符咒。这里,我们可以设身处地想,归属于其他文明实体的人们首先会问:当你们这么说的时候,究竟是在什么意义上指延续不断?是指语言方面的延续不断吗?或者指族群上的延续不断?还是指一种文明在精神世界所达到的高度与广度及其造成的历史效应持续不断?族群及其语言在历史上的延续或中断充满偶然性,并不取决于它们自身的内在特性。在相对封闭的地理条件下,一些非常落后的族群及其语言一直延续至今,成了人类学考察的对象,成了人类理解初始状态的参照物。这种延续虽然很长,保持了高度的自我同一性,但是,这种延续只是空洞的物理时间的延展,没有内容,或者内容极其单一。所以,他们的历史几近于重复性的循环。只是大自然的偶然原因,使他们得以延续他们这种贫乏的生活与几近循环的历史。相反,一些族群及其语言曾经创造出辉煌的文化,比如古希腊人及其古希腊语,他们不仅发明了哲学-科学的思维形态,而且创造了复杂的生活世界,教化了马其顿帝国与罗马帝国,并且通过为近代科学的发展准备了基础而继续影响着世界。但是,它自身却消失在这些被它教化的庞大帝国之中。今天,已经找不到苏格拉底、柏拉图所属的那个族群意义上的希腊人,他们所使用的希腊语也已中断为一种“古典语言”。这表明,族群及其语言(文字)的悠久历史与古老同一性既不取决于这一族群文明的内在生命力,也不表明这一文明的外在延续力。实际上,一种文明的历史效应是持续的还是中断的,是复杂丰富的还是简单重复的,是世界性的还是地区性的,完全取决于这种文明本身的内在创造力所赋予自身的生命力。而一种文明或文化的内在创造力则展现为它持续的自我突破力。一种文明的每一次自我突破都赋予自己新的生命力,因为它的每一次突破都是为自己准备更高新生的起点。所以,一种文明的这种自我突破同时也是一种自我提高、自我告别、自我断裂,因而总伴随着自我重估。在这个意义上,一种文明的真正延续绝对不是语言与族群保持简单的自我同一性,恰恰在于它自身具有自我突破的断裂能力。因此,一种文明的真正延续必基于断裂。不过,也并非所有突破都能保障一种文明的长久持续。只有当一种文明在认识与觉悟上的突破达到了足以使它造成世界性历史效应的高度与强度,这一文明才会获得长时段的持续性。文明的伟大突破不在于辉煌的物质成就,比如高耸的建筑、广袤的疆域,巨大的工程,而首先在于在精神世界打开了全新的境界,而一个根本的跃升就是发现了世界的绝对性事物与普遍性原理的存在。正是这种跃升,使一种文明能够产生世界性的历史影响。首先是对绝对性的发现,才使一个文明跳出单纯的功用世界而见证到了绝对性事物:尽管它不可吃不可喝不可用,甚至捉摸不定,它却是最可靠、最真实、最高级而超出了人们日常生活打交道的一切事物。据此,一个文明才在人群中重新唤起绝对的依赖感——这种绝对的依赖感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却在每个人的成长过程中经由沉沦于日常功用事物而被埋藏于生命深处。现在,洞见到绝对性事物的文明就象一道光芒一样划破了人们的日常世界,唤醒沉睡在人们生命中的绝对依赖感,并重新提供了一个足以让人们绝对依赖的领域。唤醒绝对的依赖感与提供绝对的依赖域是同时发生的事件,或者说,实现突破的文明是以打开一个足以承接绝对依赖感的超越域的方式重新唤醒人们的绝对依赖感。在这里,人们可以安放自己的一切希望或期待,可以从中获得经受与忍耐一切遭遇、不幸的绝对性力量。因为一个文明一旦实现向绝对的超越域的突破,那么这个文明族群便打开了“第三只眼睛”:看到了只能看到日常生命之生与死的世俗眼睛看不到的东西,那就是超越日常生命之生死的绝对性存在,并能从这种绝对性存在所能提供的各种可能视角反过来理解、对待、评判、定位日常生活。相对于这第三只眼睛,日常生活世界里的一切,包括成败与生死,都是相对性的事物。因此,这个世界的一切都可以放下或忍耐而有所坚守、有所决断、有所行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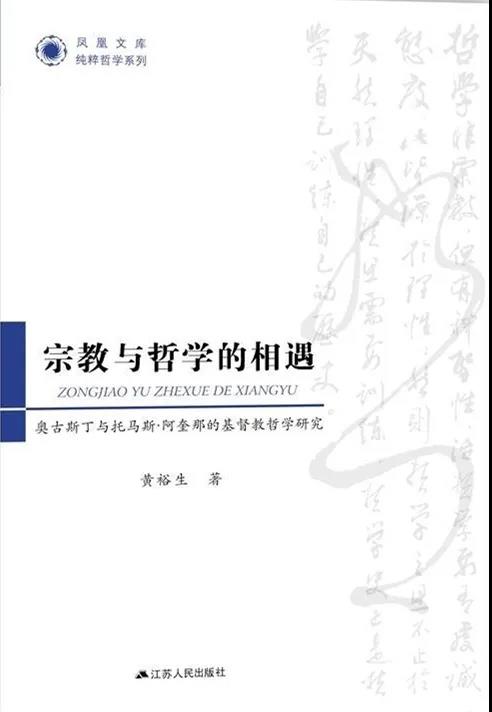
黄裕生《宗教与哲学的相遇——奥古斯丁与托马斯可奎那的基督教哲学研究》
实际上,我们要进一步说,一个文明一旦跃入了绝对性领域,它在打开人们的第三只眼睛的同时打开了一个第三方:每个人在自己的生活世界里不仅遭遇到他物、他人,也同时会遭遇到绝对者的身影,祂甚至以不出场的方式无时无处地出场。因此,祂总在人与人、人与物之间,而在根本上,人们甚至首先处在与祂的关系之中,才进入与他人、他物有关系。这意味着,每个人实际上都以一个绝对的第三方为中介发生与他人的关系,而这进一步意味着每个人对他人的态度、行为同时就是对第三方的态度、行为,而人们之间的聚集实乃聚集于第三方。由于这是一个纯粹而中立的第三方,因此,祂在纯化人们之间的关系的同时,以任何其他事物都无法达成的方式造就了人们之间牢不可破的团结。这是跃升入绝对域的文明能够在归属这一文明的人群中注入一种足以支撑经受一切苦难而穿越历史的伟大力量的秘密所在。一种文明的伟大突破还体现在第二个方面,那就是对普遍性事物的认识与承担。正如人们在生活世界里首先发现并与之打交道的是各种相对性事物一样,在与他人关系上,人们首先发现并践行的是各种特殊原则,因为人们在生活世界里相互之间总是发挥着各种不同的功能,处在由此特殊功能规定的各种特殊关系里。因此,人们最初只关注之间的特殊关系,而则混然无觉于之间的普遍关系。在这种功能性关系之外,自觉到普遍性的关系而发现人与人之间存在着普遍性原则,这是一个文明实现由特殊性精神向普遍性精神跨越的突破性提升。随着对普遍性关系与普遍性原则的自觉和发现,这一文明也就开始要求人们承担起这些普遍原则而践行之的努力。因此,贯彻、履行普遍性原则成了一项需要承担的事业。而要有效承担起这一事业,首先必须帮助更多人理解、认识那些普遍性原则。于是,便有了教育事业的确立。教育事业的确立需要有两个前提:一个是认识到人需要教育,另一个是认识到有需要通过教育来显明与确立的内容,这就是超越利益与功用的真理或道理。但是,实际上,只有认识了后者,也才能认识到前者。因为只有认识到超越利益与功用的普遍性原理,人们才会发现,由特殊性关系与特殊性原则主导的生活世界只是一个实然的世界,生活于其中的每个人过的都只是实然的生活,而这个实然世界并是一个好的世界,每个人的实然生活并不是好的生活,需要按那普遍的道理(真理)来加以改善。但是,又只有通过让尽可能多的人认识、自觉到这些普遍的道理,才可能根据这些道理来改造生活世界。这个时候就意味着,人是需要教育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只有当一个文明跃升入普遍性领域而确立了普遍性原则,发现了普遍性的道理,才会开启以革新世界为使命的教育事业,并且也才会相信教育事业而把希望寄托在教育事业上。正是因为开启了这种以明普遍道理于普天之下并据之以革新世界为使命的教育事业,并确信这样的教育事业,一个文明才真正迈进了伟大文明的门槛而具有教化万民万族的抱负与能力,也因此而必定产生持久性的历史效应。如果说洞见、亲证了绝对域的突破使文明获得了足以承受一切不幸而能穿越历史的超越性视野与绝对性力量,那么,认识与发现普遍性事物则使文明开启了足以教化万族万民而超越血缘、地域的教育事业。只有这样的文明才有可能把历史带上不断打开、升级普遍性意识、普遍性观念、普遍原则的轨道,从而把历史塑造为朝向更高普遍性方向的世界史。什么是世界史?世界史不是全球史,也即不是把全球所有地区、所有民族或国家的历史按物理时间加以编排的汇集,而是人类经历的每一个普遍性环节逐渐展开的进程,或者说,是一个通过对普遍性原则的发现与升级来展开普适性自我教化的历程。世界史的时间不是物理时间,因此它不是以物理时间来平面式地铺展、编排各个地区、各个国家的历史事件,而是按观念时间,也即按普遍性原则或普遍性观念的展开所达到的环节来划定时代。世界史在根本上既是普遍性事物的普遍性水平不断提高的历史,也是人类自我教化的水平不断提升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世界史首先是那些首先认识到普遍性事物的那些民族及其文明奠定的,并且是由最先完成向更高普遍性环节突破的民族及其文明引导的。就此而言,没有对普遍性事物的发现与认识,就没有世界史。而这样的世界史实际上也就是先进史:首先发现普遍性或者最先突破普遍性的既有环节而提升普遍性,从而走在人类的前面而教化着人类。实际上,对绝对域与普遍物的觉悟是人类实现的一次存在跃动或存在跳跃,它标示着人类从相对性与特殊性的生活世界里解放出来,跃入了一个能够不断打开、也需要不断打开的世界:绝对域是能够且需要不断接近的,普遍性是能够也需要不断提升的。在这里,对绝对的接近与普遍性的提高,实际上是同一件工作的两个方面。因此,实现存在跃动的文明既包含着对绝对域的觉悟,也包含着对普遍性事物的认识。只是不同文明在实现这一跃动时突显的方面可能会有所不同。在古代,有四个文明实现这种存在的跃升,这就是希腊文明、希伯来文明、印度文明与华夏文明,我们称之为本原文明。其中,希伯来文明突显的是绝对域,而华夏文明(以及希腊文明)突显的则是普遍性。就没有对普遍性事物的发现与认识就没有世界史而言,我们也可以说,有了实现存在跃动的文明,才启动了世界史:人类史从此展现为普遍性事物不断升级的进程。但是,就任何普遍性环节都将被包含在更高普遍性环节里而言,这意味着每一个最初实现存在跃动的文明都将持续被包含在世界史的进程之中而延续着其生命与影响。因此,一个文明的生命力与持续性在根本上取决于它是否实现了存在的跃,也即是否达到对绝对的超越域和普遍物的觉悟。因为唯有这种自觉才能参与开辟、引导着世界史而被包含在世界史之中。对于这种文明来说,哪怕创造它的族群及其语言中断了,它也一样会延续在世界史之中而继续参与对世界史的规定和塑造。在这个意义上,文明的生命力及其真正延续,重要的不在语言与族群的悠久不断,而在它打开了足以开启、规定世界史的展开内容与展开方向的真理面相与精神高度,以致无视这种文明,就无法理解世界史的整体事实,无法真正看清当今世界的由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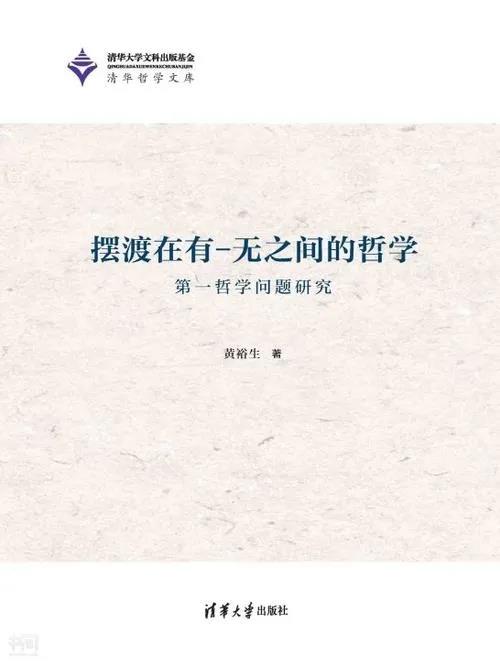
黄裕生《摆渡在有-无之间的哲学——第一哲学问题研究》
就此而言,人们能说希腊文明没有延续至今吗?不能!古希腊人通过其伟大的哲学探究活动发现了真实的存在物不在别处,只在纯粹的概念之中,也即在具有自我同一性的概念之中,从而发现了物的普遍性,走向了探究物的普遍性世界的轨道。这也就是科学的探究道路。我们甚至可以说,科学这种特有的理论化文明形态就是希腊人在哲学的探究活动中发明的,它规定了近世科学诞生的轨道。今天,全世界都在享受它带来的好处,人们没有理由说它断了。只有科学存在,古希腊人奠定的希腊文明就会在人类史上继续发挥无法取代的作用。同样,人们能说希伯来文明断了吗?且不说基督教、伊斯兰教这两个迄今仍是影响世界最大、最广的宗教文明都来自希伯来文明,靠其信仰延续至今的犹太民族对近世以来的人类的贡献不仅是全方位的,而且也是巨大的。实际上,正是“两希文明”的融合造就了近世的现代性思想与现代性社会,在把作为构建社会秩序之基础的原则体系提高到一个新的普遍性水平基础上,让全人类迈向了自我解放而迈进了平权的全球化时代,使人类以从未有过的规模与程度分享到从未有过的繁荣与自由。实际上,希腊文明与希伯来文明不仅没有中断,相反,它们一直参与规定世界史的内容与方向,并在近世暴发出前所未有的力量而影响着全人类。面对这样的本原文明,同样作为本原文明的我们,需要敞开胸怀认真面对,而不应以唯一延续的文明自居而自傲于其他本原文明之外。据说,史学界是基于三个方面来认定中华文明为唯一延续不断的文明:一,传统的语言文字未曾根本改变而保持同一性;二,以这种传统语言文字书写的古典文献一直被保存至今,未曾湮没不传;三,这些文献所传达的价值观延续至今,没有中断。在这个认定中,语言文字的同一性实际上被作为一种文明连续性的基本要素,这样规定文明的连续性,当然没问题,可存为一说。但这样的规定除有量身定制的嫌疑外,更重要的是这种规定显然过于外在与表面。因为这样的规定实际上突出的只是一种文明在物理时间上的延伸度,而未能标明出一种文明的内在力量及其外在效应。一种文明的内在力量在于它打开的精神高度与揭示的真理面相是否构成了一次存在的跃升,从而使它获得了足以开辟普遍性事业的外在力量。所以,一种文明的真正持续性不在于其族群及其语言文字保持同一性,而在于它能不断把历史带向更高的普遍性,哪怕最初表达它的语言被其他语言所替代,它所达到的精神高度与真理性也一样使它仍能继续开辟历史。因此,文明的延续性重要的不在于语言文字在物理时间的长时段自我同一,而是内在于历史的长时段效应。实际上,具有这种延续性的文明必定既具有自我连续的能力,也具有自我断裂的能力。因为一种文明要能保持影响、规定历史展开的力量,它必须有能够自我更新、自我提高的能力。但是,当且仅当一种文明对世界达到超越的绝对域的觉悟与洞见,它才能在揭示真理的同时,打开一个永远有待于打开的整体之域,从而永远为自己留下了可以继续举高投远的空间-余地,这种文明才有自我更新、自我提高的可能,而不致于或封闭于眼前的苦难,或沉溺于当前的幸福而不可自拨。在世界史上,任何一种文明都不可能不遭遇其他文明的挑战、入侵,通过自身的努力或者通过兼容其他文明来提高自己对真理的更多维度的揭示,达成对更高普遍性原则的自觉,是应对这种挑战与入侵的唯一出路,当然也是一种文明继续保持历史效应的唯一出路。就这种自我更新、自提高是基于原有的超越性基础而言,这是文明的一种自我连续;而就这种更新与提高是真理的扩容与普遍性的升级而言,又是文明的一种自我断裂。在这个意义上,一种文明的延续性必定包含着自我断裂,包含着新的内容,而绝不只是简单的不变与物理时间上的不断。简单说,文明的延续性在于它持续的自我更新以及由此造成丰富多样的持续历史效应,而不在古老的同一性与悠久的单一性。因此,如果我们要证明自己文明具有特别的延续性生命力,那么,不能停留在摆同一,显古老,说悠久,而应当显明我们的文明对世界的认识与觉悟是否达到超越的绝对域与普遍性这一层面?是否开启了追寻普遍性事物的事业?是否揭示了真理的多维面相?是否具自我更新、自提高、自我断裂的能力?特别是,是否开辟了长时段丰富多样的普遍性历史?如果无法回答这些问题,黑格尔关于中国文明与历史停留在简单的重复这一批评就无法反驳,因为不管是语言文字的同一性,还是价值观的始终如一,都可以被定性为“简单的重复”。的确,不仅文字语言的悠久同一性无法显明一种文明的延续性力量,而且这种文明所确立或蕴含的价值观的持久性也同样无法表明它的延续性生命。因为价值原则有不同层次,有些是永恒的而具有持续性力量,而有些则是时代性的,甚至很大部分(比如很多伦理习俗层面的价值原则)是时代性的。如果后面这个层面的价值原则持久不变,那么恰恰不是这一文明的延续性生命力的证明,反倒验证了黑格尔的停滞说。即使是在永恒性层面的价值原则,每每也必随着一种文明的自我提高、自我更新而被重新解释,从而获得更丰富的意义与更智慧的运用。因此,文明的生命力并非仅仅体现为它的价值原则的不变性,更体现在它的价值原则的普遍性水平及其自我更新、自我丰富、自我升级的能力。每个民族都可以为自己所属的文明感到自豪,但是,在为自己的文明自豪时,有必要把自己的文明置于世界其他文明之中来审视,以避免在自豪中陷入无知与轻狂。如果人们在为自己的文明与历史自豪时,却无视其他文明的伟大与辉煌,无视世界史的整体事实,那么,必在失去参照系的同时失去了自我反思、自我提高、自我改善的方向与可能。结果会是什么?整天活在自我虚构出来的无限自豪里,带着百年不变的狭隘、无知与狂热继续在这块土地上演绎着轻外、仇外的“文化义和团”的故事。这是需要警惕的。所有本原文明在自我肯定、自我期许的同时,都需要警惕过度的自我中心、自我优越、自我拣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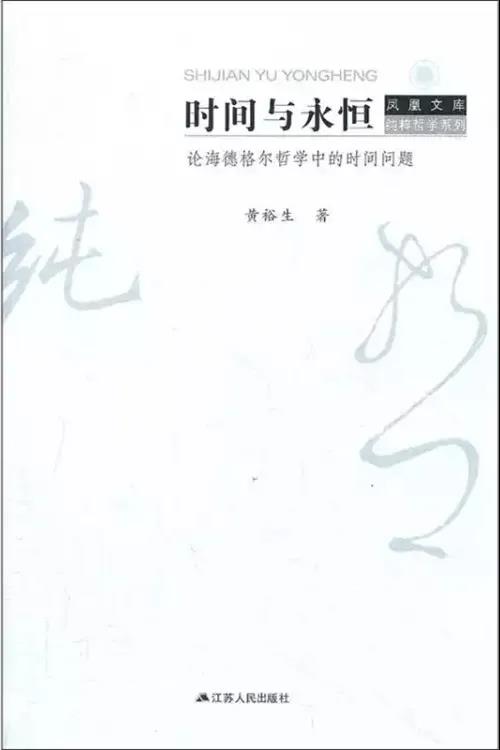
黄裕生《时间与永恒:论海德格尔哲学中的时间问题》
在“国学热”的今天,“中华文明是世界唯一延续不断的文明”成了“口号”,成为“常识”,成了“定论”,甚至可能很快会成为不可讨论的“绝对正确”。与此相应,沿袭两千多年的家天下的皇权统治也不再是“专制政治”,不再是“集权统治”,而是“贤能政治”、“王道政治”、“文明政治”。因此,有不少学人想要通过重修“中国政治思想史”来接续中国的“伟大思想”,以便使中国与世界的政治重新“文明化”。什么叫“文明化”?化夷狄为华夏,谓之文明化。何谓夷狄?无君臣礼乐之邦是也!分而言之,粗野之人,蛮荒之地,谓之夷狄。这意味着,不仅世界(当然首先指西方世界)处在粗野蛮荒之中,中国也由于近代以来深受西学浸染而夷狄化,所以,需要再度“文明化”,并且附带着也把世界“文明化”。试图以中国思想来参与塑造历史,甚至改造世界,这样的思想抱负当然值得肯定与尊重。但是,如果我们对世界史何以走到今天这样子,没有足够深刻的理解与反思,特别是,如果我们对塑造世界史发挥着巨大作用的两希文明没有足够深入的理解与消化,尤其是,如果我们对近代西人在政治思想领域所达到的高度与广度没有足够全面的把握与自觉,所有这类抱负都是可疑的,都难免走向坐井谈天。这无异于今天的中国化学家无视近代化学成就而直接回到古代锻丹术,却不仅想解决今天中国企业所需要的化工技术难题,而且还要解决世界性的化学前沿问题。在这个时代,拒斥人类近代的政治哲学思考及其确立的原则与理念,无视它所带来的席卷全球的实践运动及其建立的全新秩序,而试图回归“君臣礼乐”式的“政治文明”,不仅是极其盲目的,也是极度危险的。如果再做一个比喻,那么这实际上无异于关起门来,整天在自家院里自编自演帝王将相的大戏,在获取帝王将相的尊荣的同时,想象着全世界跪拜在君王脚下的良好秩序与高度文明。但是,院墙终归难掩现代世界的真实,难挡人类新时代的撞击,这种帝王将相戏终归是一场迷梦。既然如此,与其沉迷于帝王将相的尊荣里,不如明智地走出自编自演的故事,张开眼睛直面世界文明,直面历史时代,放弃以戏剧的方式把自己和少数人抬高为帝王将相来获得虚假的豪雄情怀,而以进入现代文明的方式来获得自信以及与他人一样的尊严。基于人类近代政治思想开辟出来的现代性社会在把人类从各种王权的专制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同时,也使人类从各种权威、各种迷信的控制下摆脱出来,每个人类个体不仅获得了一样的尊严,也获得了一样的自由。同等的尊严与同样的自由(权)成了所有人共同的出发点,也成了所有人生活与行动的底线。人类由此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一旦走上了,没有人会回头,因为没有人会愿意退回去当人下人,没有人愿意倒回去被奴役。如果说有人想倒回去,那么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这个人自己认定自己是君王,并渴望当君王。但是,任何一个认定自己是君王的人,不是骗子,就是疯子。今天的人类被带进了全球化时代,这是由包括近代政治思想在内的“现代性文明”开辟出来的一个全新时代。全球化是今天每个文明实体的现实处境。这意味着,每个文明实体都需要面对这一现代性文明,需要深入这一现代性文明,才能理解、看清自己所属文明的真实处境。在这个意义上,每个文明族群都只能通过深入现代性文明的深处才能更好地理解、重估自己的文明传统,以便确定自己所属的文明体系在这个全球化时代能提供什么,能延续什么,能超越什么,能参与什么,能承担什么。这种深入,就是一种洗礼,就是完成古今之变,就是在为自己所属的文明体系能在全球化处境下继续延续下去做出努力。全球化时代实际上既为所有文明体系相互呈现、相互照面提供可能,也为所有文明体系参与开辟、塑造世界史提供契机。这个契机不在别处,就在完成古今之变的努力里。古今之变的实质就是普遍性水平的提高,更具体地说,就是把构成社会秩序基础的那些原则体系升级为现代性文明的版本,也即升级为更高普遍性的版本。我们的文明体系要继续参与承担世界史的契机也同样在完成这个古今之变里,而不在什么“唯一性”里,更不在返回古典或复古的努力里。
2019年10月11日初稿
2020年4月8日定稿
【黄裕生 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本文原刊《中国文化》2020年春季号)

